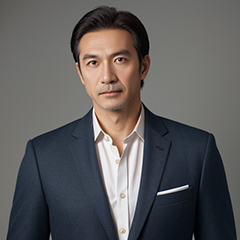律图审稿专业委员会3轮严审
律图审稿专业委员会3轮严审
我和朋友签了一份合同,后来我们闹上了法院,现在我已经知道该合同无效了,想要撤诉。我问下已经确认合同效力能否撤诉呢?
问题相似?点击查看诊断报告~
律师解答
共3条
-
 咨询我专业法务在线帮92人赞同了该解答
咨询我专业法务在线帮92人赞同了该解答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确认合同效力案件依其案件性质而言,属于确认之诉。合同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该合同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不能调解。但根据第九条的规定,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因此,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人民法院在调解时可以不考虑诉讼请求,不考虑合同效力,只要当事人满意,能达成一致,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没有损害到国家、本集体经济组织、本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的利益的情况下,这又未尝不可。
其次,对于该类型的案件,人民法院的判决并不能真正的约束到当事人,如果双方不愿意人民法院审查合同效力问题则双方可以协商让原告撤诉,即便是人民法院不准撤诉作出判决,双方也可以达成新的妥协方案,不追究对方责任,法院也只有听之任之,无计可施。再就是庭外和解也不是解决问题的百灵草,因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经过人民法院审查,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双方当事人还可能因新的争议再次起诉。这样不仅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浪费人民法院的办案资源,造成“案结了事未了”,又不能实现人民法院价值和功能。归根到底,这是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私权属性所决定的,它只是一种限制流转而非禁止流转私权,并且私法它奉行的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故民事法律法规也赋予了民事主体较大的自由,公权力的干预也是有限的。并且对双方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也应当视为对其不合法的行为所作的纠正,并无不妥。
综上,笔者认为,像本案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恶意规避法律,没有损害到国家、本集体经济组织、本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的利益,应当予以确认。全文14 2018-03-0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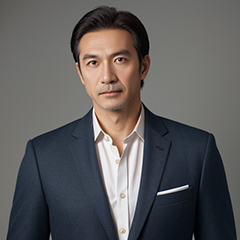 咨询我温州答疑法律助手评分5.0 “态度非常好”你好,针对确认合同效力能否撤诉的问题,我的回答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件一般不宜调解结案,普遍做法为引导当事人庭外达成新的协议以取代争议的协议,然后由原告申请撤诉。如庭外不能达成一致则及时作出判决,不主动主持调解。其秉持的观点为,合同的效力问题只能由人民法院宣告,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不属于私法领域内意思自治的范畴。全文7 2018-03-03
咨询我温州答疑法律助手评分5.0 “态度非常好”你好,针对确认合同效力能否撤诉的问题,我的回答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件一般不宜调解结案,普遍做法为引导当事人庭外达成新的协议以取代争议的协议,然后由原告申请撤诉。如庭外不能达成一致则及时作出判决,不主动主持调解。其秉持的观点为,合同的效力问题只能由人民法院宣告,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不属于私法领域内意思自治的范畴。全文7 2018-03-03 -
 咨询我合同事务法务团评分5.0 “解答有耐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立案后应该怎样撤诉这一问题,解答如下:民事诉讼撤诉的方式及条件如下:
咨询我合同事务法务团评分5.0 “解答有耐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立案后应该怎样撤诉这一问题,解答如下:民事诉讼撤诉的方式及条件如下:
1、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必须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内容明确的申请。申请撤诉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对自己的诉讼权利加以处分的具体体现,故需有内容明确的意思表示,才有可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2、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目的必须正当、合法。依照处分原则的要求,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方为有效。因此,原告申请撤回起诉亦须以正当、合法为前提。也因如此,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并不会当然地产生撤诉的效果,而需由受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并在此基础上裁定是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3、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必须基于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所谓基于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指申请撤回起诉必须是原告主动、自愿所为,而不能是被动、违心所致。因此,任何人(包括审判人员)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原告撤回起诉,也不得说服、动员原告撤回起诉。
4、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最迟应在受诉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提出。不论是当庭宣判,还是定期宣判,均应如此。这样既可使原告有较为充分的斟酌时间,慎重地适时实施撤诉行为,同时又可避免因原告于宣判后再提出撤诉申请而损及受诉人民法院所作判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为判决一经宣告,即便尚未发生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亦不得随意撤销。全文1 2020-11-05 05:54:52
文章涵盖面广,如需要针对性解答,可立即咨询小助手

咨询助手
24小时在线
投诉/举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解答仅供参考,不代表平台的观点和立场。若内容有误或侵权,请通过右侧【投诉/举报】联系我们更正或删除。
展开
看完文章仍有疑惑?试试向律师咨询吧~

律图法律咨询24h在线
认证律师:18万+帮助人次:15亿+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律师24小时在线,咨询后将为您解答。
24小时在线为您提供咨询解答
立即提问
近7日解答 7.8w 次 · 平均回复速度 3 分钟
热门问答·合同事务
问题没解决?125200人选择咨询律师



我已经知道合同无效,已经确认合同效力能否撤诉呢?
一键咨询
-
136****8817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6****3424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嘉兴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宁波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8****8856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衢州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0****0648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5****0260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3****2041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舟山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金华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湖州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丽水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衢州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8****5167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
-
湖州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4****3084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台州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杭州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5****7705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1****1438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丽水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8****8620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宁波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6****1616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8****2845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4****1625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8****5856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嘉兴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舟山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舟山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8****2123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0****3461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宁波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5****5828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湖州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1****7420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5****6430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舟山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2****3413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金华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6****1068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台州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温州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8****4346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8****0247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宁波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丽水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湖州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温州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嘉兴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1****5707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丽水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3****5650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6****3637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舟山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2****6642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4****0021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3****8451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嘉兴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湖州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杭州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4****6136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6****0637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3****8706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3****0125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台州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1****6146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衢州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1****7005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8****2436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2****0556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衢州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6****6177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台州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4****1425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台州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衢州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杭州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1****7074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2****2787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湖州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6****7862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金华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温州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绍兴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2****1200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7****8478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杭州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0****3671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台州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8****6150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嘉兴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台州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宁波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6****8824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湖州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7****8236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2****2116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金华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
为您推荐
苏州177****4986用户4分钟前已获取解答
沭阳177****7781用户3分钟前已获取解答
南京181****3011用户3分钟前已获取解答
怎样知道劳动仲裁是否已经生效
我国法律对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有很多相关规定的,我们可以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本篇文章的内容来了解一些和怎样知道劳动仲裁是否已经生效,劳动仲裁流程是怎样的相关的法律规定。
10w+浏览
 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自己写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吗
[律师回复] 一般来说,自己写的房屋转让协议,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那就是有效的。具体来看:
1. 协议双方得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是协议有效的基础。比如成年人,精神正常,能独立进行民事活动。
2. 协议内容要明确清楚。像房屋的基本信息,如位置、面积等,转让价格多少,付款方式是一次性还是分期,交付时间等关键条款都得写明白,而且这些条款不能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冲突。
3. 房屋转让要办相应登记手续。没办登记手续,合同效力不受影响,但对抗不了善意第三人。
另外,如果协议里存在欺诈、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等情况,协议可能无效或者可以撤销。
总之,自己写的房屋转让协议符合这些条件,通常就是有效的。不过为防止后面出现纠纷,最好在签协议前找专业律师咨询一下。
1. 协议双方得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是协议有效的基础。比如成年人,精神正常,能独立进行民事活动。
2. 协议内容要明确清楚。像房屋的基本信息,如位置、面积等,转让价格多少,付款方式是一次性还是分期,交付时间等关键条款都得写明白,而且这些条款不能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冲突。
3. 房屋转让要办相应登记手续。没办登记手续,合同效力不受影响,但对抗不了善意第三人。
另外,如果协议里存在欺诈、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等情况,协议可能无效或者可以撤销。
总之,自己写的房屋转让协议符合这些条件,通常就是有效的。不过为防止后面出现纠纷,最好在签协议前找专业律师咨询一下。

3w浏览
假结婚私下签的协议有效吗
[律师回复] 关于假结婚私下签的协议在法律上的效力,通常是存在争议的。
1. 可能有效的情况:要是协议内容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并且是双方真实意愿的体现,那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会被认定有效。打个比方,协议里清楚约定了假结婚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像财产怎么归属、债务谁来承担等,而且双方都签字确认了。
2. 可能无效的情况:要是协议内容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例如为了躲债去假结婚,这种协议可能就会被判定无效。
总之,假结婚私下签的协议有没有效得看具体情形,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要是对协议的效力心里没底,最好去咨询专业律师,这样能得到准确的法律意见。
1. 可能有效的情况:要是协议内容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并且是双方真实意愿的体现,那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会被认定有效。打个比方,协议里清楚约定了假结婚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像财产怎么归属、债务谁来承担等,而且双方都签字确认了。
2. 可能无效的情况:要是协议内容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例如为了躲债去假结婚,这种协议可能就会被判定无效。
总之,假结婚私下签的协议有没有效得看具体情形,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要是对协议的效力心里没底,最好去咨询专业律师,这样能得到准确的法律意见。

3.8w浏览
车祸私下解决协议书有没有法律效应
[律师回复] 1. 要是私下解决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想法的体现,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里那些强制性的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那这份协议书就是有法律效力的。
2. 协议书里得把事故的经过、责任怎么划分、赔偿的金额以及支付的方式等重要内容都写清楚。
3. 双方签字或者盖章以后,协议书就开始生效了。不过为了防止后面出现纠纷,建议可以找个第三方来做见证,或者去进行公证,这样能让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更强。
4. 如果有一方事后后悔了,不想按协议来,那另一方就可以根据这份协议书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按照协议去做。
5. 但是呢,如果这份协议书存在欺诈、胁迫这种情况,或者明显不公平,那受到损害的这一方就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把这份协议书撤销掉。
2. 协议书里得把事故的经过、责任怎么划分、赔偿的金额以及支付的方式等重要内容都写清楚。
3. 双方签字或者盖章以后,协议书就开始生效了。不过为了防止后面出现纠纷,建议可以找个第三方来做见证,或者去进行公证,这样能让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更强。
4. 如果有一方事后后悔了,不想按协议来,那另一方就可以根据这份协议书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按照协议去做。
5. 但是呢,如果这份协议书存在欺诈、胁迫这种情况,或者明显不公平,那受到损害的这一方就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把这份协议书撤销掉。

4w浏览
如何知道劳动仲裁是否已经生效
我们的工作、学习甚至平常生活过程中,相信会遇到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本篇文章对我们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作出了具体的法律知识解答,希望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帮助您了解更多与如何知道劳动仲裁是否已经生效相关的法律方面知识。
10w+浏览
 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财产公证协议会有法律效应吗
[律师回复] 1. 财产公证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像经过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以及文书,一般都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当然啦,要是有相反的证据,而且这个证据足够推翻该项公证,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公证机构会按照法定的程序,去审查财产公证协议,看看是不是真实、合法。只要公证完成了,这个协议在法律上就有比较高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3. 不过呢,如果存在欺诈、胁迫这类让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或者协议内容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算做了公证,也没办法让它有法律效力。
4. 总而言之,合法有效的财产公证协议是受法律保护的,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签订协议之前,当事人得保证自己的意思表示是真实、合法的,别因为协议有瑕疵,最后引发法律纠纷。
2. 公证机构会按照法定的程序,去审查财产公证协议,看看是不是真实、合法。只要公证完成了,这个协议在法律上就有比较高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3. 不过呢,如果存在欺诈、胁迫这类让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或者协议内容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算做了公证,也没办法让它有法律效力。
4. 总而言之,合法有效的财产公证协议是受法律保护的,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签订协议之前,当事人得保证自己的意思表示是真实、合法的,别因为协议有瑕疵,最后引发法律纠纷。

3.8w浏览
快速解决“合同事务”问题



自己写的协议书去公证处有效吗
[律师回复] 关于自己写的协议书去公证处公证后的效力问题,这里给大家讲一讲。
1. 一般来说,自己写的协议书公证后是有效的。公证主要是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确认和证明。打个比方,就像是给这份协议书盖了个“合法章”。经过公证的协议书,在法律上的证明力会更强。要是之后发生了纠纷,法院更容易相信这份经过公证的协议书。
2. 不过要注意,协议书本身的内容得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要是协议书里有违法或者不合理的条款,就算经过了公证,法律也可能不认可它。
3. 总之,自己写的协议书去公证,只要内容合法合规,通常是有效的,但不能保证绝对有效。具体是否有效,还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1. 一般来说,自己写的协议书公证后是有效的。公证主要是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确认和证明。打个比方,就像是给这份协议书盖了个“合法章”。经过公证的协议书,在法律上的证明力会更强。要是之后发生了纠纷,法院更容易相信这份经过公证的协议书。
2. 不过要注意,协议书本身的内容得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要是协议书里有违法或者不合理的条款,就算经过了公证,法律也可能不认可它。
3. 总之,自己写的协议书去公证,只要内容合法合规,通常是有效的,但不能保证绝对有效。具体是否有效,还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3.3w浏览
女方已经怀孕了 但男方有家庭
[律师回复] 1. 沟通协商:与男方坦诚交流,了解其想法和态度,共同商讨对怀孕及双方关系的处理方式。
2. 考虑妊娠:若决定继续妊娠,需思考后续孩子抚养、经济支持等问题;若不打算继续妊娠,应尽早咨询医生,了解相关医疗流程和注意事项。
3. 寻求法律帮助:咨询专业律师,明确自身法律权益和可能的法律后果,尤其涉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等问题。若男方不愿承担抚养义务,女方可向法院起诉要求其支付抚养费。
4. 道德伦理考量:思考这种情况对各方的影响,以及自身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
5. 规划未来:制定包括经济、住房、抚养等方面的未来规划,若需独自抚养孩子,要提前做好物质和经济准备。
6. 情感支持:寻求亲友或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保持身心健康,确保做重大决策时保持清醒理智。
2. 考虑妊娠:若决定继续妊娠,需思考后续孩子抚养、经济支持等问题;若不打算继续妊娠,应尽早咨询医生,了解相关医疗流程和注意事项。
3. 寻求法律帮助:咨询专业律师,明确自身法律权益和可能的法律后果,尤其涉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等问题。若男方不愿承担抚养义务,女方可向法院起诉要求其支付抚养费。
4. 道德伦理考量:思考这种情况对各方的影响,以及自身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
5. 规划未来:制定包括经济、住房、抚养等方面的未来规划,若需独自抚养孩子,要提前做好物质和经济准备。
6. 情感支持:寻求亲友或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保持身心健康,确保做重大决策时保持清醒理智。

3.8w浏览
怎样知道劳动仲裁是否已经生效
当前的社会中,在就业、出行、购物等各种情形时,都是可能会遇到一些法律权益被他人侵害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多学习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这样在面对这些法律问题时我们就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权了。在本文内容中我们对怎样知道劳动仲裁是否已经生效进行了解答,希望能解答您的问题。
10w+浏览
 劳动纠纷
劳动纠纷盗窃50000左右,羁押30天了现在已经取保,赃物已经归还,警察和我说我这个有一定概率可以缓刑,我这个缓刑概率大吗,没有前科,也是初犯
[律师回复] 您好!这边是盐城律师事务所

5w浏览
别人打了我,目前没有赔偿能力,准备写一个欠条应该怎么写
[律师回复] 写赔偿欠条时,关键要明确赔偿金额、还款时间、双方身份信息等要点。以下是参考示例:
赔偿欠条
甲方(被打方):
姓名:[你的姓名]
身份证号:[你的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你的电话]
乙方(打人方):
姓名:[对方姓名]
身份证号:[对方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对方电话]
鉴于[具体日期],乙方在[具体地点]与甲方发生冲突,导致甲方受伤。经双方友好协商,就赔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赔偿金额: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赔偿款共计人民币[X]元整(大写:[大写金额])。此赔偿款包含但不限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因本次伤害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还款时间:乙方应按照以下方式向甲方支付赔偿款:
- 第一期:在[具体日期1]前,支付人民币[X1]元整(大写:[大写金额1])。
- 第二期:在[具体日期2]前,支付人民币[X2]元整(大写:[大写金额2])。
- (如有更多期数,依次罗列)
违约责任:若乙方未按照本欠条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赔偿款,每逾期一日,应按照未付款项的[X%]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X]日的,甲方有权一次性要求乙方支付全部未付赔偿款及违约金,并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
争议解决:如双方在本欠条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欠条自双方签字(或按手印)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按手印):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签字/按手印):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赔偿欠条
甲方(被打方):
姓名:[你的姓名]
身份证号:[你的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你的电话]
乙方(打人方):
姓名:[对方姓名]
身份证号:[对方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对方电话]
鉴于[具体日期],乙方在[具体地点]与甲方发生冲突,导致甲方受伤。经双方友好协商,就赔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赔偿金额: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赔偿款共计人民币[X]元整(大写:[大写金额])。此赔偿款包含但不限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因本次伤害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还款时间:乙方应按照以下方式向甲方支付赔偿款:
- 第一期:在[具体日期1]前,支付人民币[X1]元整(大写:[大写金额1])。
- 第二期:在[具体日期2]前,支付人民币[X2]元整(大写:[大写金额2])。
- (如有更多期数,依次罗列)
违约责任:若乙方未按照本欠条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赔偿款,每逾期一日,应按照未付款项的[X%]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X]日的,甲方有权一次性要求乙方支付全部未付赔偿款及违约金,并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
争议解决:如双方在本欠条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欠条自双方签字(或按手印)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按手印):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签字/按手印):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3.5w浏览
已经履行视为合同已生效吗?
已经履行不是合同已生效的条件,合同在双方签字之后已经生效,如果是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生效的时间,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生效,如果没有规定,一般是合同签订之后就生效,合同终止的事项包括清偿,解除等。
10w+浏览
 合同事务
合同事务已经赔偿违约金的合同是否还有法律效力呢
我们的衣食住行,因为有了法律规则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各自的权益不被侵害,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法律的,因此应该提高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认识,避免在遇到法律问题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许您现在面临着已经赔偿违约金的合同是否还有法律效力呢的问题,希望本篇文章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您。
10w+浏览
 合同事务
合同事务就是我签写了一份电子合同我想知道有没有法律效应
[律师回复] 我们是具有10年重、特大刑事案件侦查经验,专职律师执业超过23年的资深律师,特别擅长经济类犯罪的辩护、解决各类重大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纠纷。具体情况可以电话沟通

4.2w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