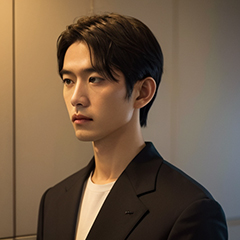律图审稿专业委员会3轮严审
律图审稿专业委员会3轮严审
你好律师,朋友之前为了一些利益上的争夺,采取了一下行贿行为,现在即将被判刑,在此之前他想要免除处罚,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行贿人下可免除处罚的情况
问题相似?点击查看诊断报告~
律师解答
共2条
-
 咨询我法律难题破解助手74人赞同了该解答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相比而言,行贿案件要宽松很多,仅要求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不要求自动投案,从宽幅度也更大,这主要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笔者认为,“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并非一律免除处罚,不能排斥减轻处罚,司法人员应依法行使裁量权。剔除“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这一情节,其他情节较轻的,当然可以适用免除处罚;其他情节严重的,一般只能适用减轻处罚。行贿情节除了行贿数额外,还应综合考量非法获利、行贿次数、对象、领域等要素。
咨询我法律难题破解助手74人赞同了该解答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相比而言,行贿案件要宽松很多,仅要求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不要求自动投案,从宽幅度也更大,这主要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笔者认为,“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并非一律免除处罚,不能排斥减轻处罚,司法人员应依法行使裁量权。剔除“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这一情节,其他情节较轻的,当然可以适用免除处罚;其他情节严重的,一般只能适用减轻处罚。行贿情节除了行贿数额外,还应综合考量非法获利、行贿次数、对象、领域等要素。
二、免除处罚不同于法定不追诉
刑法第37条规定了免予刑事处罚与非刑罚措施,其前提是“犯罪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即免除处罚针对的是犯罪、免除的是刑罚。
而刑诉法第15条列举的6种不追诉情形均应视为无罪。其中,第1种情形“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与刑法第13条的但书一致;第6种情形“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法律排除了刑法,刑事责任包括刑罚和非刑罚,即不用承担任何刑事法律后果。可见,免除处罚与法定不追诉有着罪与非罪的本质区别。
实践中,司法机关常常将行贿的免除处罚误认为第1种或者第6种情形,并以刑诉法第15条为依据,侦查机关不立案或者撤销案件;公诉机关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法院作出无罪判决。上述做法实际上是混淆了免除处罚与法定不追诉。正确的做法是:侦查机关应根据刑诉法第107条立案侦查;公诉机关应根据刑诉法第173条第2款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法院根据刑诉法第195条第1项作出有罪判决。
三、免除处罚与非刑罚应并重
忽视非刑罚是行贿无罪化的一大诱因。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对行贿免除处罚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对行为宣告有罪,不判处刑罚,但给予非刑罚处罚;二是对行为宣告有罪,既不判处刑罚,也不给予非刑罚处罚(单纯宣告有罪)。全文12 2018-08-2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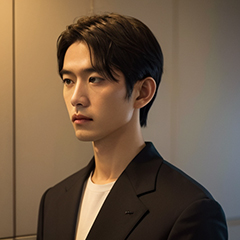 咨询我鹤壁法务评分5.0 “解答有耐心”根据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犯行贿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390条第2款同时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全文9 2018-08-27
咨询我鹤壁法务评分5.0 “解答有耐心”根据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犯行贿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390条第2款同时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全文9 2018-08-27
文章涵盖面广,如需要针对性解答,可立即咨询小助手

咨询助手
24小时在线
投诉/举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解答仅供参考,不代表平台的观点和立场。若内容有误或侵权,请通过右侧【投诉/举报】联系我们更正或删除。
展开
看完文章仍有疑惑?试试向律师咨询吧~

张润洁律师在线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擅长“刑事辩护”类问题,提问后将为您解答。
朋友又行贿的举动,但是想免...
立即提问
近7日解答 236 次 · 平均回复速度 49 秒
热门问答·刑事辩护
朝阳区尾号2669,2分钟前咨询问题
海淀区尾号8767,3分钟前咨询问题
丰台区尾号6139,4分钟前咨询问题
西城区尾号4385,4分钟前咨询问题
东城区尾号1387,1分钟前咨询问题
昌平区尾号3228,2分钟前咨询问题
问题没解决?125200人选择咨询律师



朋友又行贿的举动,但是想免罚,请问行贿人下可免除处罚的情况
一键咨询
-
175****1761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鹤壁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4****8256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周口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三门峡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7****5082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信阳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濮阳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驻马店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鹤壁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驻马店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濮阳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鹤壁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8****0418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4****0244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
-
158****5023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周口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8****0171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5****8122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郑州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洛阳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2****4020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漯河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1****2826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8****2650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0****4067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洛阳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4****2777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新乡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7****3030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4****7257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商丘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平顶山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7****0465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5****6728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0****5216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驻马店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8****4541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7****3437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鹤壁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安阳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郑州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洛阳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安阳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1****6254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1****0373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1****4541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1****3415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0****7023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鹤壁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8****8628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驻马店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郑州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焦作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平顶山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2****4708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商丘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新乡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三门峡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1****4012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开封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鹤壁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5****8871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1****1624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焦作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三门峡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8****2466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6****3043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1****6643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0****1662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安阳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洛阳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三门峡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驻马店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信阳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2****4543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平顶山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3****3742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郑州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1****0361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5****8387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漯河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4****8265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7****5156用户1分钟前提交了咨询驻马店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8****1602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1****2806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商丘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洛阳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8****2004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7****0054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濮阳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52****8765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31****6137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三门峡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76****7366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0****3606用户2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60****8360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濮阳用户4分钟前提交了咨询144****0677用户3分钟前提交了咨询
为您推荐
房山区181****8648用户2分钟前已获取解答
朝阳区152****1299用户3分钟前已获取解答
东城区180****7859用户3分钟前已获取解答
行贿罪可以免除处罚吗
行贿罪是否可获免除刑罚行贿虽可获得豁免刑罚,然而这仅限于特定情况下。如行贿者在被追究责任之前,主动坦白行贿行为,可考虑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在这些情形中,如果行贿行为较轻,对于破获重大案件具有决定性意义,或者具备重大立功表现,则应考虑减轻或完全免除处罚。
10w+浏览
 刑事辩护
刑事辩护脾切除七级能赔偿多少钱
[律师回复] 脾切除七级属于工伤伤残等级里的七级。赔偿金额得根据具体情况来算,通常包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以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
具体来看:
1.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13个月的本人工资。
2.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来定。
另外,还可能有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等其他费用赔偿。具体赔偿金额得结合当地标准、本人工资等因素综合计算。
要注意,不同地区赔偿标准可能不一样。要是想知道准确的赔偿金额,建议去咨询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或者专业律师。
具体来看:
1.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13个月的本人工资。
2.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来定。
另外,还可能有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等其他费用赔偿。具体赔偿金额得结合当地标准、本人工资等因素综合计算。
要注意,不同地区赔偿标准可能不一样。要是想知道准确的赔偿金额,建议去咨询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或者专业律师。

4.7w浏览
快速解决“损害赔偿”问题



我租个浴池,房东不知道承租人又转租给我,现在已经构成了非法转租了,我应该怎么能要回来租金
[律师回复] 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向次承租人出租房屋,是否构成非法转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若按你所言,已经构成非法转租,那应该是在出租人不予追认转租效力,且不同意你代为支付房租,并执意要求收回房屋的前提条件下。对于这种情况,一般可以要求承租人向你返还已经支付的租金,并按照你和承租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

4.4w浏览
单位行贿罪可以免处罚吗
根据相关法规,单位行贿罪在特定情况下可获豁免。若单位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主动、坦诚交代行贿行为,法院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从轻或减轻刑罚。尤其在犯罪情节轻微、对破获大案有关键作用或存在重大立功等特殊情况,法庭可考虑减轻甚至豁免刑责。
10w+浏览
 刑事辩护
刑事辩护你好:82年参加工作,92年7月份请事假参个月后到94年7月写申请退职。公司批复按自动离职处理,并除名。现达到退休年龄。请问94年以前工龄可视为缴费年限呢?谢谢!
[律师回复]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一般来说,这种情况94年以前的工龄不完全视为缴费年限,具体分析如下:
- 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的政策:在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职工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但职工被除名或自动离职后,原工作单位不再负责支付其退休费,重新参加工作后,连续工龄重新计算。
- 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后的政策:《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1995〕104号)明确,应以各地实行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作为除名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所以,如果当地实行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是在94年之前,从实行个人缴费的时间起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和缴费年限,之前未缴费的工龄不能视同缴费年限;如果当地是在94年及以后才开始实行个人缴费制度,那么94年以前的工龄一般不能视同缴费年限。
- 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的政策:在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职工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但职工被除名或自动离职后,原工作单位不再负责支付其退休费,重新参加工作后,连续工龄重新计算。
- 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后的政策:《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1995〕104号)明确,应以各地实行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作为除名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所以,如果当地实行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是在94年之前,从实行个人缴费的时间起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和缴费年限,之前未缴费的工龄不能视同缴费年限;如果当地是在94年及以后才开始实行个人缴费制度,那么94年以前的工龄一般不能视同缴费年限。

3.9w浏览
不签劳务合同辞退的员工有补偿吗,想了解:不签劳务合同的情况下,员工权益如何保障
[律师回复] 您好,看您这边具体的工作性质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如果是劳务关系,一般来说辞退是没有补偿的,若构成劳动关系,则可以要求补偿金或者赔偿金。
3.9w浏览
单位行贿罪可以免处罚吗
根据相关法规,单位行贿罪在特定情况下可获豁免。若单位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主动、坦诚交代行贿行为,法院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从轻或减轻刑罚。尤其在犯罪情节轻微、对破获大案有关键作用或存在重大立功等特殊情况,法庭可考虑减轻甚至豁免刑责。
10w+浏览
 刑事辩护
刑事辩护交了七八年企业社保后失业后又交了六七年灵活就业社保,现在又进企业交三四个月社保刚好满五十岁退休年龄能这样完成退休吗?
[律师回复] 您好,请问您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

3.6w浏览
快速解决“劳动纠纷”问题



行贿罪怎么免于刑事处罚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行贿者主动交代罪行可从轻或减轻处罚。若犯罪情节轻、对侦破重大案件有关键作用或立功显著,可减轻甚至免罚。行贿者自首并符合条件,有望获宽大处理。
10w+浏览
 刑事辩护
刑事辩护想了解,我的车卖给别人了,钱没有付清,他又把车卖给另一个人,说好的每个月给我转钱,只有开始的时候给我转过两次,后来再没有转,现在都快一年了,不给我钱也不接我电话
[律师回复] 你好,可以起诉要求给付购车尾款

3.4w浏览
快速解决“债权债务”问题



对方寻衅滋事,入室伤人还携带凶器,被我不小心弄成轻伤,现在派出所要求协商要我赔偿15万,我方不同意,我想咨询下这种情况判正当防卫的利率大不大?
[律师回复] 我们是具有10年重、特大刑事案件侦查经验,专职律师执业超过23年的资深律师,特别擅长经济类犯罪的辩护、解决各类重大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纠纷。具体情况可以电话沟通

3.5w浏览
行贿罪如何免于刑事处罚
行贿罪免刑考量复杂,涉及受贿动机、金额、社会危害、认罪态度及贡献等。自首、如实交代罪行、积极退赃可视作悔过,可能从轻或免刑。若无严重负面影响且有显著贡献,法院亦可能酌情免刑。
10w+浏览
 刑事辩护
刑事辩护